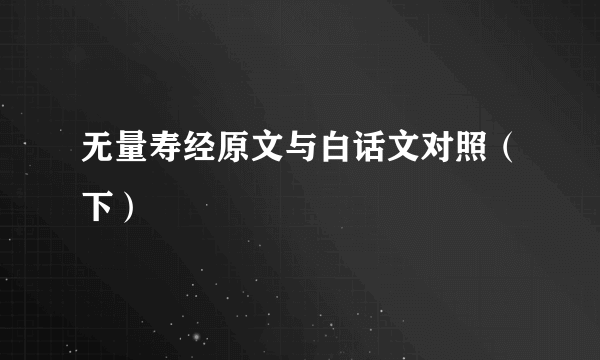李春阳:为什么会发生白话文运动?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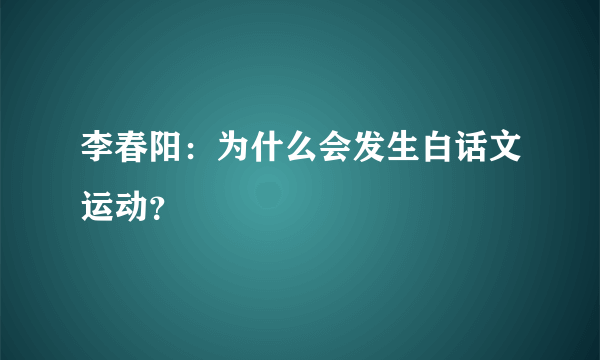
李春阳《能不忆寒山》纸本设色2014年 中国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Vernacular Movement),如果承认胡适是首倡者,那么这场波澜的初潮之涌实际上发生在美国。本来是几位留学生之间关于文字和文学的争论,由于胡适将它们写成通信和文章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而广为人知。胡适《逼上梁山》一文言之甚详,不必赘述。过去官方的教科书说它发生于“五四前后”,这一说法特别耐人寻味,它实际上在暗示白话文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联系,但以史实探究,这一少数人提倡的文体革新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日发生的群众游行毫不相关。如果一定要把它与某个“大写日期”联系起来共同注释历史,应当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民国的成立,使少数得风气之先的人觉得应该以一种新的书面语言来写作了。二十世纪,系列大事相继发生,起先取消了科举考试,使八股文没了出路,接下来宣统皇帝退位,中华民国甫一成立,立刻颁布大总统令,强迫剪辫,禁止缠足,一时间移风易俗气象一新,虽然政治在实质上实现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体制变了,一整套术语也不得不跟着变,推翻帝制给国人带来的鼓舞是时下的人无法想象的,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个效应。帝制下的表达方式乃是公车上书,只有先取得国民资格,才可以上街游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包括多种注音字母方案,皆是上奏朝廷,希冀得到圣上的认同,一纸诏书下来,风行天下。民国之后,这个途径断绝了,于是主张便以报刊杂志直接面向公众,陈独秀同意胡适之并与之呼应,本是两人相契,与君何涉,但由《新青年》公之于众,而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公共言论空间的建立,给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以可能,有没有这样的言论空间,乃是帝制和民国的根本差异。
“划时代”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20世纪的中国人似乎非常热衷于定义和重新定义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连一般的文章作者,也染上这一恶习。实际上定义时代的权力,并不掌握在我们任何人手中。“五四”已经被最高权力定义为“划时代”了,白话文运动自然可以分享这一无上的光荣。以白话做书面语,并不自今日始,白话小说即使从明代起算,也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当初胡适与梅光迪、胡先驌等人的分歧主要在白话能不能做诗这个问题上,所以才有《尝试集》的写作和出版,白话诗是写出来了,成为了名著,但是否就意味着成功了呢?诗人胡适,并不为人认可。胡适之后,还有更多的尝试者,白话能写诗么,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也不少,一九六五年毛泽东给陈毅信中明确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当然,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白话写诗,假若还不好说成功,白话写小说么,五百年前已获成功,然而那是先人的成就,论者匆忙宣布的“白话文的胜利”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后来几乎所有论者,亦皆认为白话文运动成功了,这成功又指的是什么呢?
文言与口语在先秦时代的真实状况,至今无从确定。为何《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关于“白话文运动”的词条断定“文言文是古人口语的摘要”呢?根据我的研究,是根据鲁迅《门外文谈》的观点,然而,鲁迅当初审慎、推测的语气不见了,更由于一九四九年后鲁迅先生不可怀疑的权威性,此说俨然成为定论。而白话文运动之初的纲领性理论,即采取西方语言学对文字的定义:文字是声音的记录,是语音的符号,而西方文字属于“表音文字”,“语音中心主义”占据语言的主导地位,文字是语音的附属。但是,汉字是“表意文字”,不存在“表音文字”的类比性。吕叔湘早年曾说:“文字的起源大致和语言无关,”并且“一部分文言根本不是‘语’,自古以来没有和它相应的口语。”但长期以来,这一认识未能得到传播和重视,于是以西方文字定义硬套汉语和汉字,乃相沿成习,铸成共识。语言学研究著作《马氏文通》以印欧语性质为标准看待汉语,“把印欧语所有而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朱德熙语)。由此可见,始于“言文一致”的倾向,在百年汉语研究中未得到质疑,而视之当然,直至近年 , 有人从理论上提出汉语的“字本位”,认为文言为口语摘要的判断,出于西方的语言观。
语言为全民所共有,无阶级性,此乃语言学界的共识。若说西方“语音中心主义”是白话文运动主动上当的第一次,那么,第二次便是语言学的所谓“阶级论”。五四时期,文言被指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语言,白话是人民的语言,由此二分,意识形态话语于焉形成,“文言”从此被判决为腐朽的、落后的、统治阶级和没落文人所使用的死语言。否定文言文,与否定由文言文所书写、记载的儒家经典(当不限于儒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又道,“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今日读这些话,偏激之甚,错谬之深,已无须辨析了。
书面和口语的不一致,自古已然,明清尤甚,其原因在于文言文写作以复古为时尚,唐宋八大家便是明清作文的楷模。但白话文的滋生与蓬勃,亦正在此一时期。之所以文言与口语的不一致成为问题,是与西方语言接触后,两相比较的结果。语言学的进化论,一度被国人奉为真理,而作为印欧语言之特色的“言文一致”,成为改造汉语的最终诉求,这一努力至今未见成效。现代白话文,依然言文不一致。朱德熙认为,五四之后的白话文学作品也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有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言文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汉字是形意文字,而非写音文字,除非采用拼音取代汉字,否则永远不可能一致。走拼音化道路,曾经在数十年时间是国家文字改革的方向。越南、朝鲜、韩国、日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去汉字化”运动。
《古代汉语》绪论认为,古汉语有两个书面语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形成的古白话。”徐时仪的《汉语白话发展史》,是系统探讨汉语白话发展史的著作,在文白长期并存的古代汉语书面语系统中,将白话的历史分为露头期(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宋元)和成熟期(明清)。事实上,汉语第一次与印欧语言的接触从东汉佛教入传便已开始,梵文不但影响了汉语对音韵的重视,且佛经的汉译所形成的“内典”,也成为首个与文言文发生形成差别的独特文体。王国维认为楚辞、内典、元剧的文章,在美学风格上可鼎足而立。《朱子语类》乃朱熹门人记录其讲学语录的汇编,为使听者易于理会,语不求深,多方设喻,如话家常,以明白显豁为追求。记录者虽难免加工,仍保存了大量时语。以口语宣讲理学,由此成为一种传统,王阳明《传习录》即为一例。朱熹阳明以达意为目的,文言便任其文言,白话亦任其白话,没有非此即彼,或以彼此的高低相较。至于明清是否出现过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颇费争议,中国历史自具轨迹,套用西方历史模式,有蓄意误导之嫌,况语言的发展演变,与资本主义何涉?“市民阶级”一语也嫌牵强,城市人口或可统计,是否称得上阶级,尚存疑问。明清章回小说的古代白话与文言一样,属书面语系统,认为明清章回小说使用的是一种不同于文言的“白话书面语”则可,若说他们“用当时口语来书写”则未必。今天的白话文也不是以今天的口语书写,有谁会像新闻联播那样说话的么,但写起文章来,却不自觉与某种腔调保持惊人的一致。书面语和口语的界限不容混淆,白话书面语,也并不等于口语,其差别在于一是用来阅读,一是用以倾听,“目治”与“耳治”有别,岂可不论。由于广播电视网络视频等技术手段的出现,我们还须区分“原生口语”和“次生口语”的不同,媒体上的“领导讲话”“辩论会场”“谈话节目”“主持人语”以口说的形式传达,但并非真正的口语,有时被讥为“不说人话”其实自有不得已之处。
其实,白话文并不局限于通俗文学。上述佛家的“变文”“俗讲”、儒家的“语录”虽则通俗,但不在文学之列。文言亦非一成不变,之所以长期居于“独尊”地位,乃因文言能够顺应历代语言的变化而变化。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明显不合先秦语法,明证唐朝的口语到底还是侵入了文言。钱基博评梁启超政论体有言:“酣放自恣,务为纵横轶荡,时时杂以俚语、韵语、排比语及外国语法,皆所不禁,更无论桐城家所禁约之语录语、魏晋六朝藻丽徘语、诗歌中隽语、及南北史佻巧语焉。” 梁体不仅为当时报章杂志争相刊发,今时台港海外中文报刊依然沿用其绪,并无难懂之弊。此可见推断文言与白话自古以来的对立,是虚构的、夸张的,更未有文言与白话之间不可间容的紧张仇怨。文与白、书与言,曾经长期共存、并行、辅助、长育,虽偶或相犯,但井水河水,两相活泛。是故白话文运动从颠覆到成功,一跃而据至尊地位,进而废除文言,也许可视作某一底层叛逆故事在语言变革中的假想剧情。
把明代的四大奇书视作通俗文学,本身即为新文学运动的偏见,汉学家浦安迪称之为“文人小说”乃卓异之见,更准确的看法是民间流传过程中多次加工的文人小说,在此问题上若还存在争议的话,那么《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等伟大白话经典作品广为人知之后,硬说白话文“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就太不顾事实了。曹雪芹和吴敬梓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他们以娴熟的白话书面语写作之时,从来不知什么叫做文言独尊,略早于他们的蒲松龄以文言撰写《聊斋志异》,亦绝不会看不起白话。科举考试不以文言、不写八股不行,而创作特别是著小说,以白话还是文言悉听君便。四大奇书问世经已百年,白话章回体小说的伟大传统,在十六世纪奠定,寂寞了一个世纪再次焕发异彩,经过李卓吾、毛宗岗、金圣叹、张竹坡等人评点鼓吹,《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白话文体,已与庄骚史记并列成为经典。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说,“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瘵《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 此书据推断最晚于一八九五年公开刊行,此前已广为人知,作者做过十年外交使节,又以“诗界革命”之倡见重于仕林,此论一出,影响之巨,不难推想。以欧洲近代民族语言从中世纪统一的拉丁语中分离而出的例,对照汉语的自我更新,对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思路,发生决定性影响。胡适后来即有此类比。裘廷梁著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把书面语和口语的分离,当作大问题,可谓是对黄氏论述的回应。所谓“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然而,从今时汉语依然不能言文一致的现状看,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毕竟属于西方表音文字的议题,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安不上这一题,若要改革,也未见走得通西方这条路,硬要去走,不但言文仍然不一致,亦且伤害了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