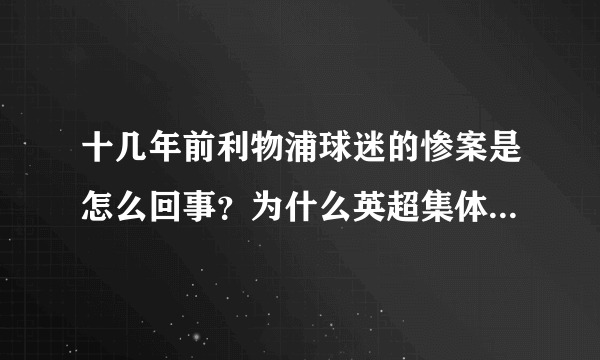曾宝仪:我见证了一场“想了十几年”的死亡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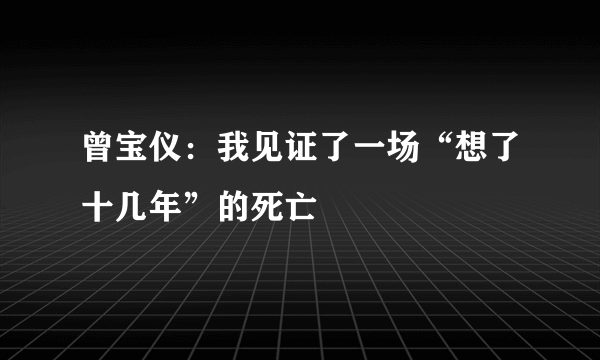
“够了,我太老了。”
5月9日,大卫·古多尔(David Goodall)在瑞士巴塞尔的一间旅馆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身着一件印有“衰老不体面”字样的套头衫,宣布将于次日在当地的一家诊所接受安乐死。在全世界媒体的镜头前,人们问他想要在死时放什么音乐。古多尔回答:非要放的话,那就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吧。说完,他突然用德语歌唱起来:“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
歌声中,很多人哭了。台湾主持人曾宝仪正在和腾讯新闻拍摄一部与安乐死有关的纪录片,也在发布会现场。“我有点被吓到了。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大,充斥着整个记者会的现场。我感到他生命的能量全都爆发了出来。”
两天前,曾宝仪第一次见到古多尔。那时她刚到巴塞尔,节目组与古多尔预订了同一家旅馆。计程车停在旅馆后的花园边,曾宝仪正准备下车,迎头碰上了刚刚被推出来要去花园吃午饭的老人。古多尔坐在轮椅里,头向前倾,衰老和虚弱扑面而来。他比她想象中的老太多了。护士为古多尔准备的午饭是千层面和红茶,由于咀嚼困难,他必须要把面切成小块才能进食。曾宝仪在一旁给古多尔倒茶。她半蹲在他身边,握着可能是她这辈子握过的最老的手。
死亡议题对于曾宝仪来说并不陌生。2011年,一直照顾她生活的爷爷去世了。从那之后,曾宝仪花了大量时间探索死亡,她读书,参加灵性体验课,家中四分之一的书都与死亡有关。她自认为对死亡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但在去巴塞尔的飞机上,她仍然感到忐忑不安。亲近之人死亡带来的痛苦令她至今无法忘记。她并不能够完全理解古多尔。
104岁的古多尔获得过澳大利亚荣誉勋章,有3个博士学位,是最早研究温室效应的学者。他担任过30个生态系统杂志的主编,并参与出版超过100本书籍。他的超高龄生活看上去并不那么糟糕。102岁的他还可以在杂志上编辑论文,2015年他仍旧能够独自乘火车穿越1800公里进行野外旅行。然而在一个月前,古多尔吹灭了他的104岁蜡烛。随后,他决定计划自己的死亡。当人们一遍遍问古多尔:“真的不要留下来了吗?”他总是回答:NOT AT ALL(完全不)。
“我做了二十年的主持,从来没有访问过一个决定自己死期的人。”去瑞士前,曾宝仪在社交网络上向网友和朋友们征集意见:面对这样一个老人,如果只能问一个问题,你会想问什么?朋友们争吵起来。一些人质疑古多尔的选择:为什么他要扮演上帝的角色?
在去巴塞尔的飞机上,曾宝仪一直在设想面对古多尔时将会遇到的种种情况,但这次意料之外的遭遇令她措手不及:在镜头面前她完全素颜,没有化妆,穿的上飞机时的衣服,更重要的是,她被迫把所有假设抛诸脑后,直接抛出那个最本能的问题:“是因为跌倒,才决定要死的吗?”
多年来古多尔一直倔强地保持着独居,他在家行走时会借助一个带轮子的椅子。他早上把牛奶倒进麦片,自己清洗苹果,每周末去购物。但几个月前,独居被打破了,他在家中跌倒,大声呼救却没人听见,直至两天后才被打扫卫生的清洁人员发现。在关于衰老的书籍《最好的告别》中,作者葛文德写到:“他们(老人们)总是会跌倒。会在自己的房间,或者卫生间,或者从厨房餐桌边站起来时,突然像一棵树一样倒下。”跌倒往往成为老人生活的转折点:不仅带来的是身体的疼痛,还用羞耻、无用、丧失催促着心灵的崩塌。
曾宝仪本能地设想,在摔倒而未被发现的两天里,古多尔所面临的困境。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在巴塞尔旅馆的小花园里,阳光透过树荫洒在古多尔身上,老人平静地摇了摇头:“我已经想了十几年了。”
在花园午饭的简短聊天后,古多尔吻了曾宝仪的手,这一幕场景让曾宝仪在事后回想起来仍觉得十分温暖。不过每当曾宝仪将要沉浸在感性的遐想中时,古多尔便又会以如石板一样的清醒叫醒她:不是跌倒,是生活的全面崩塌。
衰老是不断丧失,如同河水带走沙子。30岁起,人们的心脏泵血峰值就开始逐步下降,40岁左右,肌肉的质量在走下坡路。到80岁时,人们会丢失25%-50%的肌肉,x光下的骨头逐渐透明,血管变窄,脊柱萎缩,身高比之前降低5-8cm。
在这20年间里,古多尔的视力一直在衰退。直到现在,曾宝仪甚至无法确定古多尔第二次见她时是否还能认出她来。古多尔的听力也在下降,许多问题曾宝仪需要重复好几遍他才能听清。
生理衰退带来的是精神上的剥夺感。作为学者的古多尔本来还能吸取很多知识,但身体的下滑使他失去了快乐的来源。
“缺乏流动性是我虽然没有生病就想要自杀的原因之一。”古多尔在接受访问时这样表述。他狂热地热爱旅行。但在很早以前,他便被吊销了驾驶证。
2015年进行的火车旅行被人们津津乐道,但在古多尔看来,它同样充满缺憾:“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但我更希望有一个伙伴,我很寂寞。”
衰老没有带走他,但是带走了他的朋友。古多尔在珀斯缺乏交往,他的许多朋友都离世了。他仅有的一些快乐是每周去他工作的伊迪斯科文大学在走廊与同事聊天。但在2016年,学校单方面宣布古多尔已经不适合前往办公室了,建议他在家办公。古多尔收拾了旧办公室里的书籍,这是他再也无法幸福的开始。
衰老逐一砍掉了古多尔生活中可能的全部,一个月前的跌倒又再一次攻击了他。医生要求古多尔受到全天候照顾,否则他将被转移到养老院。
“我不想去医院,我觉得医院就像监狱一样,医生可能会限制我的行动。我也不想去养老院。”古多尔这样对曾宝仪说。养老院拒绝隐私与主体性。护工安排好洗澡时间与穿衣时间。集体活动按照规定的秩序进行。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能养宠物,禁止酒,要吃软糯烂熟的食物。养老院对于古多尔来说,不是选项。
“够了,我太老了。”古多尔要抢在死神到来之前,制止衰老对他的剥夺。
早在古多尔八十多岁的时候,他便加入了EXIT INTERNATIONAL安乐死组织。EXIT的创办者菲利普·尼克与古多尔是多年的好友。在安乐死的领域内,尼克走得很极端,尼克相信理性自杀——他将理性自杀定义为具有健全思想的人因为合理地看到了自己不能接受的未来生活而选择自杀。EXIT为选择死亡的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和工具,以使他们可以在自己选择的时间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无痛而安详地离世。早在1996年,澳大利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允许晚期病人实行安乐死。但当尼克用自制的机器结束了4名患者的生命后,这一法案又很快被废除了。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安乐死都被认为是违法的。澳大利亚只有维多利亚州允许患绝症的病人安乐死。瑞士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接纳外国人安乐死的国家。古多尔尝试过3次自杀,但都失败了。原本尼克设想可以在国际水域里建造一艘死亡船来规避法律,协助人们自杀,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但最终这一想法也没能实现。于是,古多尔只能选择飞行近20个小时,到瑞士做最后的终结。安乐死的旅费是尼克与古多尔采用众筹的方式募集的,共有376人在26天为他们捐赠了20956美元。
活着和死去
死亡是个体的,只有身体真正如日落消沉之时,你才能感受其中的焦虑、无助、悲愤。但死亡又是社会的,人处在与他人的联结中,选择死就像强行斩断联系,对于活着的人而言,如同抛弃。
这种割舍的痛苦有时是巨大的。BBC拍摄过一部安乐死纪录片《如何死亡:西蒙的抉择》。英国男性西蒙在50多岁时患上了渐冻症。爱好交谈与运动的他也因此逐渐丧失了说话与行动的能力。“这太不像个男人了。”在西蒙必须要让护工帮自己洗澡穿裤子时,他这样表达。
妻子问他:真的不想留下来了吗?然而即使西蒙一遍遍在纸上写着自己活着的欲望是0%,妻子仍旧认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这只是西蒙一时因为害怕而导致的冲动选择。最终,西蒙只能以尝试自杀的方式让太太明白了他的坚定。57岁时,西蒙在瑞士接受了安乐死。
西蒙去世已经3年,不久前,曾宝仪又访问了西蒙的妻子,而她却在镜头前说自己反悔了:“我后悔让他做这件事情了,哪怕是我能多陪他一天也是好的。”在这3年里,她仍没有完全摆脱同意让西蒙去死的自责。
这一次陪古多尔到瑞士的大部分是他的孙辈,在来瑞士前,古多尔与他的其他家人一一告别。家人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孙子们在镜头面前保持积极,宣称自己为爷爷感到自豪。但事实上,“这是艰难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有什么感觉。”其中一个孙子邓肯说到。私下里,他们告诉曾宝仪,他们知道古多尔想要在最后对世界说什么,因此他们支持了这次对媒体的全程开放,并在镜头面前保持应有的样子。
在古多尔临死的前一天,他与孙辈们在巴塞尔大学的植物园里闲逛,那是陪伴了古多尔一辈子的东西。即使在二战期间,古多尔也在专心研究番茄。曾宝仪在植物园里对古多尔进行了正式的访问,摄像机架起来,古多尔用手轻抚着植物的叶子。曾宝仪猜想:“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想要一一跟这些我爱过的植物告别。”于是她问:“你跟这些植物说再见了吗?”古多尔抬起头,并没有想象中的温情答案,他冷静的说:“再见?为什么要说再见?”曾宝仪突然意识到:“我以为他在意的东西不是他在意的。”很多时候,“如果是我”的换位思考并不正确。就像西蒙的妻子认为,我们不是还可以一起看电视,一起吃早饭吗?为什么你不能缓慢地离去?而这种体贴的演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粗暴。这次访问结束的时候,曾宝仪没有说再见。她给了老人一个拥抱。她的胳膊挽过老人的脖子,古多尔长满斑点的手搭在曾宝仪身上。看到这一幕的古多尔的家人,也将手握在了一起。
古多尔告诉曾宝仪,他依然热爱自然,他还想念斐济,那里很美。在最后一个晚上,他在酒店里享用了最喜欢的炸鱼薯条和芝士蛋糕。但毫无疑问,对于他来说,死亡才是最大的期许。
安乐死执行当天,瑞士诊所的医生问了古多尔几个问题:你是谁?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你要来这个诊所?你知道用药之后的后果吗?
他平静的回答了这几个问题。输液管的开关交到了他的手上。他的身边是自己的家人,房间里回荡着《欢乐颂》。他滑动了开关。不久,医生确认,104岁的大卫·古德尔已离开人世。
在执行安乐死的当天,曾宝仪与古多尔见了最后一面。那时她的内心依旧挣扎,观看一个人的永久离别还是让她难以接受。最终,一个场景令她释然了。在执行安乐死之前,古多尔坐在轮椅里,他的孙子们在一旁签协议。也许是过程有些漫长,古多尔抱怨:“我们到底在等些什么?”孙辈们解释说还有一些表格要填,随后老人露出了无奈的表情:“唉,总是有很多表格要填啊!”
“你知道那一刻,我觉得我放下了很多。其实他就是准备好了,我为什么要站在他的旁边,用一种,‘天哪,你要去死了,好悲惨’的心情去面对这件事情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在那里好好祝福?”
(图片由腾讯提供)
大家都在看这些
是枝裕和的金棕榈:家庭伦理与煽情童年 “抢人大战”中的重庆 这部五月最火的电影,你可能还有这些不知道 鱼油保健管用吗? 全网制造“社会人佩奇” 《后来的我们》:中国父亲田壮壮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转载请联系后台 。
点击以下封面图
一键下单 「最后一个浪漫派: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