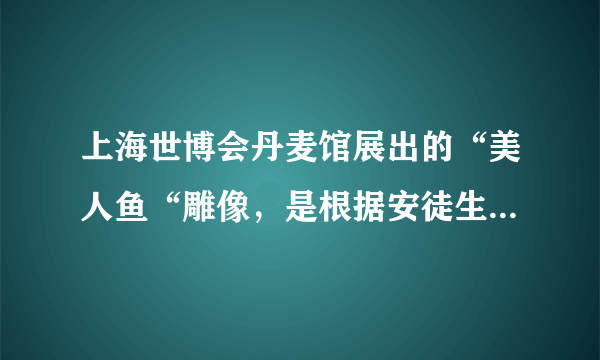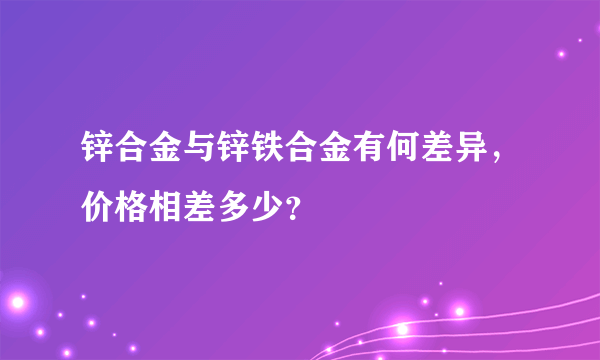鄂温克语和满语在语法词汇的差异是否要大于「蒙古语族内部语言」,同时也大于「突厥语族内部语言」的差异?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我们目前实行的语言分类从大到小是:语系-语族-语支-语种。
虽然满语和鄂温克语都隶属于满-通古斯语族,但它们是不同语支的。而谱系分类法就是建立在他们之间的异同点而做出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女真语、满语、锡伯语被分到满语支,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被分到通古斯语支。虽然都是黏着语,基本语法结构相似,也有着大量的同源词。但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中,通古斯语支出现了大量的有别于满语支的词汇。
当我学会满语书面语的时候,锡伯语和女真语的大部分词汇我都可以说是认识熟悉,赫哲语就需要记住很多特殊词汇,而鄂伦春语和鄂温克语不仅仅是背记词汇那么简单,我需要从头学习它们的语法结构。
深入研究后,就会明白为什么将两者分成不同的语支,每个语支内部的语种均有他们特有的同源词。举个例子:
以“山”为例,满语支和通古斯语支体现出了高度的内部一致性。alin和ur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来源的产物,这使得同一语族中对同一事物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类型的词汇体系。而这也本就是语支分类时的证据之一。
但作为同一语族下的语种,它们有大量的同源词,举个例子:
所以,题主在备注里举的很多例子,恰好是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同源词,而不是满-通古斯语族的。以至于会出现这样的异常,即满-通古斯语族内部词汇体系相差巨大而蒙古、突厥两语族内部相差不大。
我来按照题主在备注中提出的一些词汇使用问题的顺序简短说明一下 题主的误区 。
1、数字“万”
1)满-通古斯语族:
女真语:tumen;
满语:tumen;
锡伯语:tumen;
赫哲语:tumen;
鄂伦春语:tume;
鄂温克语:tumung.
数字“万”是满-通古斯语族的同源词,题主应该是记错了,因为鄂温克语里namaji是数字“百”。
2)蒙古语族:
蒙古语:түмэн;
达斡尔语:tum;
布里亚特语:түмэн;
卡尔梅克语:түмн;
东乡语:on/wan;
土族语:tәmeen;
保安语:uan;
东部裕固语:temen.
东乡语和保安语明显是汉语借词,除此之外,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数字“万”是同源词。
3)突厥语族:
鞑靼语:төмән;
图瓦语:түмен;
维吾尔语:tümen;
土耳其语:tümen;
部分突厥语族仍然使用着该词,甚至匈牙利语tömény、波斯语tūmān也是同意。古突厥语tümän、吐火罗语tmān/tmane、古斯拉夫语тьма、古汉语* tman均有类似的表示“模糊数量很大”的词。该词起源还不确定。
2、天
1)满-通古斯语族:
女真语:abha;
满语:abka;
锡伯语:abka;
赫哲语:abka/buga;
鄂伦春语:buga;
鄂温克语:abka/boga.
其实鄂温克语,“天”两种说法都有。但都是同源词。
而 @deyetu 老师也提到了满语中的sunggari,以及“蒙 t 满 s”之间的关系,我也认为sunggari很有可能就是tengri在满语中变化而来。在满语中,sunggari很少用,只在“银河”“天河”词组中出现,解释也是“abkai bira be sunggari bira sembi(天河之意)”,直接使用了abkai来解释sunggari。
2)蒙古语族:
蒙古语:тэнгэр;
达斡尔语:tәŋgәr;
布里亚特语:тэнгэри;
卡尔梅克语:теңгр;
东乡语:asiman;
土族语:tәŋgerә;
保安语:asimaŋ;
东部裕固语:teŋger.
东乡语、保安语和突厥语族中的“asiman”来自波斯语aseman。而其他蒙古语族中的“天”来自于古突厥语teŋri。
3)突厥语族:
土耳其语:gökyüzü/sema;
阿塞拜疆语:göy/səma;
土库曼语:gök/asman;
维吾尔语:kök/sama;
鞑靼语:күк;
巴什基尔语:күк;
图瓦语:дээр;
乌兹别克语:ko'k/osmon;
塔吉克语:осмон;
哈萨克语:көк/аспан;
吉尔吉斯语:көк/асман.
突厥语族里,“天”并不是tengri。“asiman”上边已经解释,而“gök”来自于古突厥语kök。除了表“天空”之外,它主要是指蓝色、绿色以及与之相近的颜色。比如:
雅库特语:күөх;
卡尔梅克语:көк;
哈萨克语:көк;
图瓦语:көк.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只有图瓦语的“天”既不是terngri,也不是asiman,又不是gök。дээр来自蒙古语,原意为“上边”)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词——“神”——突厥语族中为:
土耳其语:tanrı;
阿塞拜疆语:tanrı;
维吾尔语:tengri.
突厥语族中,仍然有语种保留着古突厥语中的意思。只不过传播到蒙古语族时,只保留了“天”的含义(也有“天神”之意)。
评论中有提议把楚瓦什语也列出来作为突厥语族的另类对比,我就列一下上边几个词 楚瓦什语 都是什么:
天:тӳпе;
蓝色:зәңгәр/күк;
神:тәңре.
楚瓦什语的“天”来源我不知道,突厥语族的语言我才开始接触不久,恕我无知了。但“蓝色”的күк和上边的gök一样,就不多说了。这里提一下зәңгәр,这个词来自波斯语zangâr,表示“蓝色、青色”,在突厥语族中还有其他语言也有这个词:
巴什基尔语:зәңгәр;
维吾尔语:zengger;
乌兹别克语:zangor.
而最后的“神”就很明显和tanrı一样,就不多说了。
3、白
1)满-通古斯语族:
女真语:ʃaŋgian;
满语:šanggiyan/šanyan;
锡伯语:šanggiyan/šanyan;
赫哲语:shaŋgin;
鄂伦春语:bagdarin;
鄂温克语:giltariŋ.
女真、满、锡、赫中,“白”同源。鄂伦春语的“白”来自蒙古语族,鄂温克语的“白”来自满语支。
2)蒙古语族:
比较满-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颜色“白”的词缀:
而c、s辅音交替的现象在蒙古语族内部也是存在的,比如察哈尔方言和喀喇沁方言之间。
4、题主提到的“百”
1)满-通古斯语族:
女真语:tangu;
满语:tanggū;
锡伯语:tanggū;
赫哲语:tawun;
鄂伦春语:niamaazhi;
鄂温克语:namaazh.
2)蒙古语族:
蒙古语:зуун;
达斡尔语:jao;
布里亚特语:зуун;
卡尔梅克语:зун;
东乡语:be;
土族语:jong;
保安语:nʥɵŋ;
东部裕固语:ʤuːn.
nama与tanggu来源不同,越大的数词,出现的越晚。如果该数词出现之时,语支已经分裂,那么很可能大数词会有不同源的现象。而赫哲语一度被认为应当分进满语支,就是因为它有部分词汇是和通古斯语支其他语种不同源的,就比如“百”。我记得有份论文提到过,通古斯族群在迁徙的过程中,鄂伦春和鄂温克人所居住的森林较北,而满语支族群不断南迁,进而鄂伦春与鄂温克两语在后来出现的词汇里存在不少有别于满语支的词汇。再加上,鄂温克人与蒙古交流较多,曾使用过蒙古文记事,语法词汇受到影响实属正常。
但为什么“万”这个词,满-通古斯和蒙古两语族却又是高度一致,是为同源?
我看到过几篇文章提到,tumen一词可能最原始的意思并不是指代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指明数量很大,即一种模糊的概念。因而,该词可能出现很早,早于诸语的分裂。
你举得例子是一些词汇上的例子。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搞通古斯语研究,以及搞蒙语-通古斯语语族比较研究的时候,如何确保资料的准确性。两种语言的关系,是看成方言关系,还是语言关系可能也会有争议。我对通古斯语的了解还极其有限,跟你简单分享一些我接触过的东西。关于阿尔泰语的研究在Irina Nikolaeva(2014)里有一定量的整理。这个论文收录于(The Oxford Handbook of Derivational Morphology),集中讨论整体阿尔泰语的派生特点。她在论文里呈现的通古斯语分类如下:
这个分类主要参考的文献如下:
有一些不同的分法见于:
通古斯语词汇的参考,可以参考cincius的通古斯语词典(这本书我没有),以及各种通古斯语独立成书的,但是词汇不一定都全,而且很多词的翻译(汉语,俄语,英语以及其他)可能会受到作者主管判断的影响。我经常使用的是朝克老师出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但是他这本词汇比较是以语义为主,每一行以一个语义为中心,列举出中国境内几个通古斯语(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以及资料比较有限的女真语(主要参考金启宗的《女真文词典》))的对应词汇,但这里一个问题是同一个语义对应的词不一定是同源的。这几个语言如果是一个语言分化出来的,那么一些词会在历时变化中分化为不同的语义表达,所以一个语义对应的词汇,不一定是同源的。
然后来讨论下你说的一些问题。
“另外我发现满语的万是tumen, 而鄂温克语是namaji,但蒙古语族内部都是tumen类,”
首先根据《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满语tumen一行的其他通古斯语词汇都是“tumen”的同源词。而“namaadʒ”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里是鄂伦春语和鄂温克语的“百”。
在《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Altaic Languages》当中关于“百”的一部分词源记录如下:
这里所列举的一些是通古斯语的“*namo”和蒙古语的*ǯaɣu-n。通古斯语里其他表示“百”的就是满语tanggv系的。这些词之间的关系,我就没有什么想法了。
为什么鄂温克语和满语等都被划分为满通古斯语族,而他们的“百”却不一样?
我的想法:
2. 仅就我所知,一些阿尔泰语(以及我的研究对象韩语)之间的数词存在很混乱的相关性,比如说 既然韩语和满语不是一个语族(多数人认为他们也不是一个语系),但他们的一些基数词,依旧有相似性。比如满语uyun(*uhun:9),韩语아홉 ahob(9)。满语和蒙的,二十orin,三十gvsin,四十dehi可能是从蒙语语族借的,因为蒙语的对应的二十,三十,四十和个位数有对应关系,满语的ilan和gvsin就毫无联系了。满语的“万”tumen和中世韩语(一般指的十五世纪,十六世纪这段的)的“千”tsɨmɨn长得很像,但是一个是“万”,一个是“千”,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关于问好的问题这里略过。
“满语的“天”是abka, 而鄂温克语是buga, 但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好像都是tengri。”
abka和buga可能是同源词,其分化可以用单词重音结构的变化来解释。
和蒙语tengri相关的可能是满语的sunggari(这个应该是什么论文或者书里都提过,我暂时找不到就不参考了),后者见于满语的词组“sunggari bira(天河)”,这里的sunggari指“天”,但是只在少数词组中可见,其是借词的可能性很大。满蒙语中存在大量的“蒙 t : 满 s”的对应。比如“terge:sejen(*serge)”等等
“而满语中的"白"是canggiyan(锡伯语也是这样),但鄂温克语是giltaring, 鄂伦春语是bagdaring。但蒙古语族语言中基本上都是cagan,除了青海土语和达斡尔语等语言发qigan之外。”
你想说的是这里满语的白色,看起来和蒙语族的很像,但是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的和满语的却不太一样。那么就先看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的白色吧。“giltaring”,其相关满语词汇的本意是“亮的,发光的”,
所以鄂温克语的“giltaring”可以认为是“gilta”的语义从“发亮”到“白色”的语义扩张。
关于“bagdaring”,我查到的在《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Altaic Languages》中的内容如下,
这个词在蒙语语族中是有的,但他的主要词义是“灰色”。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的bagdaring是从这里借的么?我觉得存在这种可能性。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的词汇相对来说可能要和蒙语语族更近一些,比如我刚才举得“蒙 t : 满 s”的例子,“terge:sejen(*serge)”对应的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都是近似于蒙语的terge。
而蒙语,满语,甚至于韩语,日语的白色,我觉得都有可能同源。
满语的一众单词可能词源都是“白色”,比如nimanggi(*xima),xun(*xigun),silenggi(*xile)等。
“所以我有这样的疑问,是否真的鄂温克语和满语内部的差异有这么大,又是什么造成这样的差异呢?按照这样的标准,鄂温克语和满语是否可以构成两种「语言」而不是像蒙古语族,也像突厥语族内部那样只是方言差异呢?鄂温克语和满语是不是不能像突厥语族内部语言,和蒙古语族内部语言那样可以直接通话呢?”
首先,鄂温克语和满语同源词的数量,还是足够大的,这个如果看《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这类词汇书籍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一部分鄂温克语,埃文语的单词确实和蒙语族更近,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地理上更为接近,这部分单词是古代的接触还是相对来说较近的接触,我完全不清楚。而且语系的划分也不是完全以基础词汇为基础,还要考虑语法,音系等的相似度。比如说《歷史言語學と言語類型論》(松本克己)里认为,蒙语突厥语的元音和谐都是前舌元音后舌元音的对立,而满通古斯语和韩语,吉尔亚克语等的元音和谐是ATR。从这点上来看,鄂温克语也是和满语更近。
是否能够直接通话?在彼此不懂对方语言的情况下,我觉得满语母语者和鄂温克语母语者无法直接通话,但是在对对方语言简单了解后,进行简单的日常口语交流应该很容易。这方面朝克老师应该做过很多田野,我觉得在他的一些书里应该会有提到。满语鄂温克语的交流情况。
蒙古语族内部都可以直接对话么?这个我不太了解,但我觉得可能不是单纯地直接对话。可能是某种,或者某几种蒙语的方言有较大的影响力,导致其他蒙语语族的语言多多少少都能听懂这种蒙语方言,所以能够对话。一点儿蒙语不懂的达斡尔语母语者可以和蒙语母语者对话么?不清楚。
以上不是什么科学的分析,只是我的零七八碎拾来的东西和一些我不成熟的想法,希望能给你提供帮助。你最近提的类似问题很多,我会偶尔回答下。
词汇的事大家说了很多了
我说个大家不乐意说的吧
满语
你好=saiyvn?
saiyvn是sain的疑问式
因为:你=si ;好=sain。
所以:你好=si sain。 ???
因为:你=you ;好=good。
所以:你好=you good。 ???
鄂溫克語和滿語的差異是很大啊
然而,你可知 楚瓦什語和撒拉語 愛馬格語和東鄉語 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