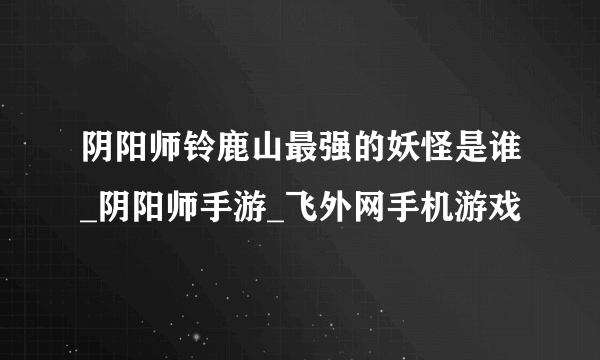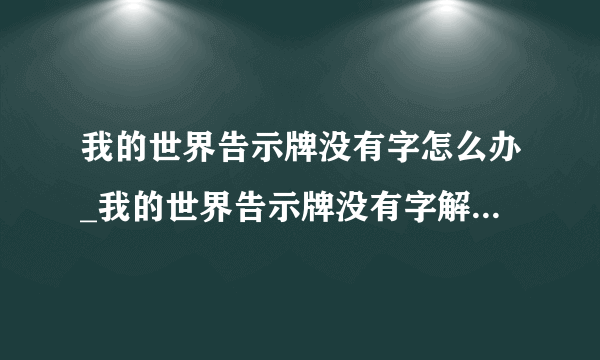嫁入豪门不是妻(嫁入豪门5年没有夫妻之实)-飞外网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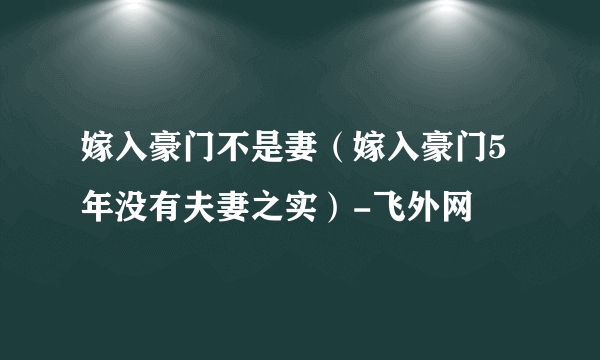
每天读点故事APP独家签约作者:黄粱
“帝王之爱,要藏起来。”父皇这句话,玄祎记了许多年。
1
景和十三年,几乎是玄祎有生以来最得意的一年。这一年,他得了世间绝色云妃,又得了旷世奇才裴少卿。直到大婚时,他拿喜秤挑开盖头,出现一张面无表情的脸,他惯常的轻笑才出现瞬间的凝固。
这是全天下最尊贵的贵女,也是他的宁王妃。
两人对视时,一温笑,一冷漠,谁都不知道,在日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们要给彼此留下多么刻骨铭心的痕迹。
2
宁王府建在城郊,占地颇广,多假山楼台,回廊遍布,无一处不精巧,无一处不繁华。
除了病梅馆。
正如这院落的名字一般,里面住着一个病的要死的宁王妃和她荒唐到可笑的寒梅气节。
病梅馆内下人寥寥,平日里也没人想去走动,那病鬼更是从不出门。要说热闹,也就只有云妃“拜访”之时,能迎来短暂的热闹。
病梅馆内。
那绝色美人与她凑得极近,近到她看得清那美人脸上的粉粒。
立冬刚过,她已披上一件旧狐腋,越发衬得身侧美人风姿飘逸。
“王妃,你说什么样的死法才是最好?”美人托腮,侧着头看她,问道。
她不答。
“你说,太子会怎么死呢?”云妃声音颇娇柔。
“子孙满堂,寿终正寝。”她眉目间皆是冷淡,声音亦冷,寥寥数语没有丝毫温度。
云妃咯咯直笑。
“王妃真是痴了。太子最好不过是一盏鸠酒,三尺白绫,最差不过千刀万剐,万箭穿心。寿终正寝,绝无可能。”
她不答。
“王妃自己会怎么死呢?”云妃又问。
这个问题,她当时没有在意,后来才用心思索良久。
当时,她只是问,“为何你们都认定太子不得善终?”
云妃颇不屑答,“你身为宁王妃竟还问出这种蠢问题,有此等处境不足为怪。”
又说,“你不如早早病死享福,为后人腾位置,也省得王爷每月心烦。”
她难得地笑了,点头道,“会有这一日的。”
太子一定能子孙满堂,寿终正寝。
千刀万剐,万箭穿心就都由她一人受。
云妃走后,她痴痴一笑,不想摧了心肝,咳了半(巴黎世家是什么梗?2020年的七夕时,Balenciaga依靠“土味广告”成功出圈,迅速在时尚圈掀起了一场流量与话题的狂欢,当时无一不在诟病七夕限定的“土味”。之后又凭借巴黎世家的经典字母袜再次火了起来,短视频平台的播放量一路飙升,让印有 Logo 的黑丝愈发受宠。)晌。
——
宁王来时,她还在咳,拿手帕捂嘴,弓着背,像只瘦虾。
云妃几乎每隔半月就要来一次,每一次,她都要大病上好几日。
仿佛云妃一心要把她耗死,而她一心要证明自己熬不死。
宁王每月都要来几日,以示对王妃的尊重,或者说,对温相的尊重。
慕仪看都不看他,只低头兀自咳嗽。
宁王亦不发一言,只坐在榻上安闲看书。
就寝亦是分床睡,整整一夜,没有人开口说一句话。
吹了灯,整个内室充盈着浓稠的黑暗,淡淡的药气总是挥之不去,固执地绕在人鼻尖。
后半夜,床上的人开始翻腾,压抑的哽咽从喉间溢出,如困兽悲鸣。
一人无声起身,跪坐在床前,用手拭去床上人脸上纵横的泪。
汗与泪混于一处,触手满是湿润的冰凉。
摸到削尖的下巴,凹陷的双颊,她突出的骨几乎硌人。
玄祎轻轻将额头贴上对方额头,轻呼口气,闭上眼。
她从前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
是他亲手毁了她。
3
宁王府最著名的人物有三,宁王妃,云侧妃,与幕僚裴少卿。
云侧妃出名在美貌,裴少卿出名在奇才。
宁王妃出名在出格。
宁王妃温慕仪在拜堂时,不拜新郎,反侧身拜向众宾客。在向淑妃奉茶时,举茶盏便摔,不奉茶,亦不磕头。与宁王也无任何夫妻之实。成婚两年,一心要自己病死在小院,外界事一概不闻不问。
向来温润翩翩的裴少卿的著名事迹“中庭之骂”由此而发。
裴少卿不屑跨入病梅馆一步,只站在中庭,大庭广众下狠狠唾弃王妃。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像汝这般不忠不孝不贞,不知礼义廉耻之人,尚有何颜面身居高位苟活于世?”
慕仪当时裹着鹤氅,轻声笑道,“只怕恶人命更长呢。”
说完,命人关门,从此门外唾骂的人渐多,但这扇门始终没有再开过。
——
偶有一日,慕仪翻一卷旧书,不期然从中落出一张小笺,右下署名是两个苍劲的金错刀,少卿。
她与裴少卿相识久矣,只是世人皆不知,也幸而世人皆不知。
少有人知,裴少卿出身相府,乃是府中一名小厮之子,无依无靠,无书可读。
慕仪发现其卓绝天资,推荐给温相,温相又送他至白鹿书院学习,这才有了今日之裴少卿。
这段关系埋得很深,知情者不过温相父子几人。
裴少卿是温慕仪手里最重要的棋子,这棋局已下至最后,棋盘上的所有人,即将散场了。
4
宁王再次踏入病梅馆时,她在喝酒。
她喝酒像喝药一般,屏息整碗灌下去,再大口喘气。
玄祎把手中纸包放至她面前,在她对面坐下。
全汴京城被巫蛊巫师搅得乌烟瘴气,唯有此处像一方净土。
难道几张符咒,几个木人真能置人于死地?信的人心怀鬼胎,怕的人心中有鬼。
全汴京城竟无一个正常人。
“王妃今日为何饮酒?”宁王问道。
她抬起朦胧醉眼,望入对方眼中。
“妾身以酒,为王爷道喜。”她举杯向宁王。
“本王何喜之有?”玄祎目光幽深,欲望穿那双眼,她眼中朦胧醉意背后,竟是一片冰冷。
“不日便有。”她勾唇一笑,头枕着臂伏在几上,笑着笑着,忽然带起几声呜咽,“可怜了我的殿下……”
这声殿下,不知指谁,是眼前的宁王,还是东宫的太子。
玄祎死死盯着她,目光近乎于恨毒,实则是浓得化不开的悲怆。
十年前在温府的九重回廊初遇时的小姑娘,五年前宫宴上戏谑合作的一阙八声甘州……
他见过她承欢相府时蹦蹦跳跳的欢脱模样,也见过她在宫中温贵妃处佯作端庄的假模假样,还见过她与太子耳鬓厮磨时的两片绯霞。
但从他掀开她大红盖头的那一刻开始,她就只剩下这一副半人不鬼的阴阳怪气。
玄祎强自按下激荡的心神,拿起搁在榻上的永远翻不完的半卷汉书,不再看她一眼。
——
你可知,他跌倒于众人之上。
又是分寝而眠,只是今日在榻上辗转的,换了个人。
玄祎梦中始终呢喃着这一句,然后在大汗淋漓中醒来。
他跌倒于众人之上。
她从来只知太子无辜,太子贤德却不得众心,太子岌岌可危,太子此生只怕难得善终。
可太子出生便有无双家世,锦衣玉食地生,或许将悲壮地死,日后有千万人在史书中为其鸣不平。
世间有多少人,苦苦挣扎着求生,默默无声地死去。
他陈玄祎拼尽半生只是追逐太子的起点。
他敬重兄长,也嫉妒兄长,也从来没有忘怀这位兄长,是不能与他共存于世的死敌。
她说不日将有喜事,可这喜事里,藏着太多人的血泪。
一个纸包“啪”地打在床榻上。
玄祎下意识地闪躲,后来才发觉这正是自己带来的蜜饯,从前她很爱吃,尽管她来宁府后再没吃过一口,但玄祎还是常常会遣人去买。
“扰人清梦。”言语虽冷,心意却温暖。
玄祎不知自己梦中说了什么,幸好她不点破。蜜饯甘甜,可解人心头苦痛。
他拆开纸包,放一颗梅子在口中。很甜,甜了整夜。
5
天气越发寒了起来。
她望着门外出神,没有在听云妃又说了些什么。
“快要结束了。”云妃也不自觉地望向屋外无比辽阔的天地。
玄祎坐在禁卫右大将军府,此刻也望向屋檐外的天际。
一阵轻风,将他们的目光连接。过去多少个无声的日夜,仿佛都在此刻放飞于风中。
——
快要结束了,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结局。
巫蛊之祸越演越烈,最后竟然祸及天子。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漂橹。
京中因巫蛊被处斩之人不计其数,汴京风声鹤唳,连那两个字都成了禁忌。
搜查的禁军去了东宫,也确实搜出了不少木人和符咒,但禁宫之中竟毫无动静。
太子这几日频频被召入宫,禁军把守四座宫门,无人知道里面正发生着什么。
天气一天天悄然转寒,汴京城在无声酝酿着一场风雪。
裴少卿领着王府众多幕僚前来请愿,禁中局势未明,甚至圣上也生死未卜,若太子此刻动什么手脚,他们动作只要略迟一刻,等太子荣登大宝,等待他们的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太子平日里再恭谨再正直,在生死攸关之时,做出再出格的事都可理解。
他们要先发制人,以护驾之名,发禁军围皇宫,重新掌控局势。
一众幕僚跪于阶下,玄祎望着一地颜色各异的脊背,轻轻地,无声地笑了。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太子是什么样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事。
他就是今世的公子扶苏。
但玄祎沉痛发声,“身为臣子,理应护驾。清君侧,斩逆臣。”
裴少卿郑重磕头,“王爷英明。”
他离至尊,只剩一步。
——
慕仪今日拿出蒙尘已久的焦尾琴,焚香净手之后,才拿松油细细擦拭,又上了弦,恢复这名琴旧日荣光。
这琴在卓文君手里时,可也是这样的光景?
她又一次弹起凤求凰,弹至曲中凤鸟清啸时,仍然下意识地停顿,等待相和的箫声再次将玉人送至她眼前。
云妃本低头玩弄玉指,闻声抬眼笑看她,“不可能有人来的。千刀万剐,万箭穿心。”
慕仪将手边香炉重重摔在地上,一地香灰。
云妃哈哈大笑。
——
五年前她走投无路找到裴少卿时,裴少卿堂堂七尺男儿跪倒在她面前,告诉她,此生,这条命都交由她差遣。
她红着眼告诉他,她只要他做一件事。
此事进一步就是万丈荣光,退一步就是无底深渊。
但无论荣耀还是地狱,她知道他都不在乎,他的心从不在世间。
可笑她把卿相之才当一卒子用。
这卒子奋不顾身,一头撞开这迷局,左突右闯,只是从来没有退路。
裴少卿跟在宁王身旁,如潮水般的禁卫军在他们身后随阵型不断聚散。
今夜无风无月,黑夜浓稠得如化不开的墨。
玄武门。
城楼上的门将点起火把,大声喝问:“来者何人?”
玄祎朗声回道,“宁王前来救驾!”
“救驾?宫中无需救驾,宁王想谋反不成?!”
玄祎不与他多言,指着城门命令斩关攻城。
禁卫军竟无一人上前。
“宁王已反,立斩于城下。”
禁卫大军齐齐转身,将宁王围于中央,闪着寒芒的兵刃围了一圈又一圈。
玄祎未着甲,依旧褒衣博带,轻衣风流。他微微一笑,与此情景格格不入,却绽放出异样风华。
“少卿,这么多年,难为你了。”
裴少卿收起假作的慌乱,闻言默然。
在这包围圈里,插翅难飞。这是没有生路的杀局,卒子终于迈出最后一步。
将军。
城楼上静静立着一个人。即使裹在厚重的貂裘里,那人仍然冷得哆嗦。
那个形销骨立,半人不鬼的人一步步走下城来。
城门开,那人出来,步步向前,禁卫军中散出一条道路,直通向宁王。
玄祎就在马上,看她一步步,一步步走来。
许是厚重的貂裘妨碍了她的动作,她走得很慢。
站定在他面前,慕仪本想大笑的,最后却没有笑。
他们默然对视,隔着命运,隔着生死,隔着过去相伴的数千个日日夜夜。
她嫁入宁王府,用五年时间,熬干自己半条命,只为了有朝一日,杀了他。
慕仪举起一只手,掌心向着玄祎,只要轻轻一摆手,千万人将上前将他的命踏得粉碎。
“慕仪,我也想活命。”
慕仪鼻尖一酸。
她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说出这句话。
她忽然想起桌上常年放置的蜜饯,虽然从未吃上一口,她也知道其中的甘甜滋味。
她其实知道深夜有人为她拭泪,也知道有人疲惫靠在她床前却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她知道他的冷淡背后,替她扛下了多少非议。
她知道他的低贱出身,也知道他一步步爬上高位曾走过怎样一段路程。
他没有丝毫过错。
怪就怪命运把他们摆在对立面,只有一人能存活。
她一定要太子活下去,她要他子孙满堂,寿终正寝,成为太庙里一幅完完整整的明君图。
即使她受千刀万剐万箭穿心,堕入地狱永生永世。
他们都没有错,那就让她一个人错到底。
掌心向下,轻轻一压。
刀刃划过皮肉,割断筋脉只要一瞬间,连喷涌而出的血液都还是温热。
她闭上眼,重重关上泪的门。
但泪水还是决堤,蜿蜒泪痕迅速爬满了面。
落马声沉重,扬起一层薄尘。
终于尘埃落定。
她睁开朦胧泪眼,正撞入玄祎深不见底的目光中。
跌落在地的人是裴少卿。
棋局上胜负已定,但他一扬手,打翻了棋盘。
慕仪跌坐在地,手脚并用,爬到裴少卿身前。地上已积聚一潭血泊,但血还在不断地从他脖颈处潺潺流出,伤口深可见骨。
“少卿……”她声音已带哭腔,她紧紧握住他渐渐发凉的手。
即使在此刻,裴少卿一双眼依旧如春水般清亮温和。他深深望着慕仪,他的气管被划破,发不出最后的声音,他就这样一直望着慕仪。
都结束了。
她拼命点头,“我知道,我知道的。少卿……少卿,你安心吧。”
她身上沾了许多血,但她毫无所觉,伏倒在血泊中动弹不得。
裴少卿在求她放下。
与她相握的手终于无力垂下。
世上少了一个卿相,少了一个痴人,少了一个卑微卒子。
慕仪摇晃着起身,宁王一直看着他们,剑还提在手上,血一滴滴顺着剑身滴落在地。
禁卫军皆已后退列阵,收剑回鞘。
宁王与她一样一身是血。
“是你……”她猛烈地咳嗽,“你早就……早就看穿了。”
宁王居高临下地俯视她,面无表情,“裴卿,云妃,拿两个人翻盘,此事只有王妃做的出。”
慕仪笑得尖利。
“你亲手杀了他,是吗?”
宁王不言,收剑入鞘,几滴血液挥洒在地。
慕仪还想说什么,但眼前忽然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
慕仪醒在一个黄昏,在病梅馆的床上。
室内空无一人。
她有片刻的茫然。
五年时光,设了五年的局,换了个满盘皆输的结局。
用尽了全力,她还是救不了太子。
她躺在床上,一直望着头顶碧纱橱。
直到最后一丝晚霞沉下西山,整个世界都陷入黑暗。
有人推门进来,走到床前。推门声很轻,脚步声也很轻。
慕仪侧头看。
是宁王。
“醒了就起来喝药。”他点亮了烛火。
“云妃在哪?”她声音哑得厉害。
“先喝药。”盛着浓黑药汁的碗递到她眼前。
“你怎么还敢让我活着?”她眼也不眨地看着玄祎,目光近痴,“是太子死了么,不然你怎么敢?”
玄祎面上淡淡,还是那句话,“先喝药。”
慕仪端起碗一饮而尽,再度凝视他。
玄祎拿起几上搁着的蜜饯,送至慕仪嘴边,“张嘴。”这次声音是柔和的,隐约带着笑意。
她侧过头去。
那只手停留许久,等不来她回头,只好收回,将蜜饯放回。
她又一次竖起了满身的刺。
“太子什么时候会死?”她背对着他,轻声问道。
胜负已定,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等了许久,等不来回应,只等来门开了又关的咿呀声。
他要怎么告诉她,太子已经死了,和皇后一起,万箭穿心,声名狼藉。
宁王靠在门上,慕仪蜷在床角。
这样的拖延,能拖到几时?
6
尽管早已料到这一刻,当婢女慌乱地跑过来时,玄祎还是方寸大乱。
“求王爷赐妾身速死。”她跪地,三拜九叩。
跪伏在地上的人只着单衣,身形极瘦,脊骨一节节突出。
“不许。”他一字一顿,说得极用力。
她抬头,目中竟已波澜不惊。
玄祎忽然感到难以名状的惊恐,三两步上前紧攥住她双手。
“王爷,妾身很累了。”她黑沉沉的眸子里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求王爷放过妾身,好吗?”
最后两字说得极轻,玄祎却忽然发了疯,“不行,不行……”
连完整的话都说不出,只知道不行,绝对不行。
但那真实的理由要如何说出口。
玄祎红了眼,望着她的眼狠狠地说,“你若敢擅自死去,温府上上下下,本王就让他们一个个通通陪葬。”
他是天命之子,是未来的皇帝。
他一言九鼎。
慕仪闭上眼,“温府……”
世人说,无声流泪时心是最痛。
那她此刻泪湿透了前襟,还兀自不停地流,是有多痛。
“今生今世,王爷都会为此后悔。”她大笑出声。
袖中寒光一闪,早已备好的匕首出鞘,划过她惨白面容,划出两道交错伤口,从额上到嘴角,半张面皮都似嘴一般翻开。
满脸的鲜血淋漓让她看上去如鬼魅般骇人,而她偏偏还疯狂大笑,用尽全身力气,声嘶力竭地尖笑。
屋外宫人皆惊恐失色,奔走告知王妃疯了。
玄祎张开双臂把她轻轻拥入怀,然后越收越紧,抱得极用力,仿佛要揉她入骨血中。
这个出格,执拗,疯狂的女人,是他结发的妻,是他一生的执念。
慕仪呜咽出声,一声声犹如困兽悲鸣。
“本王不会后悔,永远不会。”
不管怎样,只要留住她,只要她还在,不管什么模样,他都会心安。
玄祎放开慕仪,她跪坐在地,目光涣散,不知在想什么。
玄祎拾起落在地上的匕首,望着慕仪面目全非的半张脸,毫不犹豫拿刀划上自己的脸。
慕仪如梦中惊醒,劈手去夺匕首,却还是慢了一步。
原本色灿春山的一张脸,变成皮开肉绽的怪物,他蟒袍上浸满淌下的的鲜血。
慕仪呆愣良久,不知所措。
“你真是前无古人,举世无双的大痴人。”
慕仪第一次,为他落了泪,泪入伤口,钻心地疼。
7
玄祎登基时,有冠上旒珠遮面,众臣亦不敢抬头直视天颜,是以并不觉有异。
但待到封后大典时,半张疤脸的皇上,执起同样半张疤脸的皇后的手,这幅情景颇为滑稽。
所幸如此滑稽场面并不多见,帝后感情颇为寡淡,许多重要场合皇后并不出现,而交由贵妃处理。久而久之,天下人皆识贵妃,而不识皇后。而皇帝对此僭越行径也不闻不问。
许多年过去,贵妃换了许多位,皇后依旧是皇后。帝后感情依旧寡淡,只是多了位嫡长子。
魏家已不再统兵,温相也告了老。边境止战,与民生息。
前朝废太子的夙愿,在当今圣上的手中得以实现。
时光依旧时而温吞时而迅疾地往前走。
——
当年,在太子被诛之后,他的遗物过了许久才被整理出来。
唯一的一张小笺,他许下的唯一的来世,不是给她。
她与他断绝音讯五年,他以为她早已变心,故将来世许给了温五。
他可怜温五一片痴心,却不知她温慕仪的痴心更甚。
有什么东西在悄然落下。
还是那一年,先皇缠绵病榻许久,不见好转,亦不见恶化。
时近中元,玄祎献了位术士入宫,此人将在中元当夜为先帝招魂。
先帝没有拒绝。
漆黑的大殿,只有巨大的屏风后点着烛火,那术士也在屏风后,却不见影子。
一阵吟唱之后,烛火猛地摇曳起来,众人屏息凝神,纸屏风上缓缓站起一人,依稀看得清轮廓,玉冠束发,秀颀如松。只是那人身上,密密匝匝插满了箭羽,在昏黄烛火之下,阴森可怖。
“父皇!”这呼喊凄厉绝望至极,但在座之人都辨得出,这音色是何人所有。
“父皇为何不愿相信儿子!”他抖着插满全身的箭,“吾母子两人的性命竟不如你的江山重要吗?”
先帝突然发了疯,嘶吼着赶走了所有人,只他一个人留在殿中招魂。
原定招的是两人的魂,一是太子,一为皇后。
但除了先皇与术士,无人见到先皇后的仙魂,也就不知殿中人鬼间跨界的交谈。
只那一夜之后,先皇旧疾复发,数日后驾崩。
这场戏是玄祎所设计,戏词由玄祎亲手写,皮影由玄祎亲笔画。
雄才大略,纵横捭阖一世的先皇,心疾竟是自己的皇后和太子。最后又由自己的儿子,亲手点燃了他心疾,送他命归九天。
他当年告诉玄祎,帝王之爱,要藏起来。
他藏了一世的爱,骗过了世人,也险些骗过了自己。
如今世代领兵的魏家不复存在,君王心中的隐忧终于去除。若先帝泉下有知,便可坦然与皇后相处了。
8
史记,中宗皇帝玄祎在位五十三年,期间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开创天元盛世。
崩后与发妻章慧懿皇后温氏合葬于昭陵。(作品名:《山河旧事:帝王》,作者:黄粱。来自:每天读点故事APP,看更多精彩)
点击屏幕右上【关注】按钮,第一时间向你推荐故事精彩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