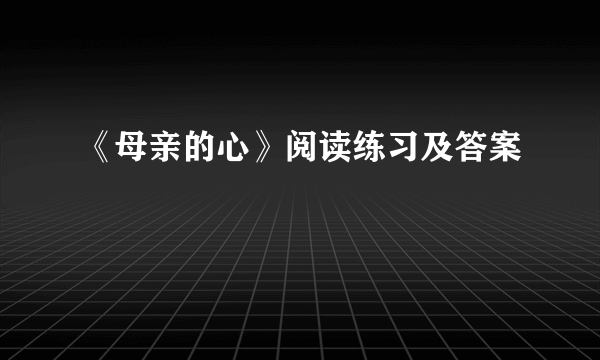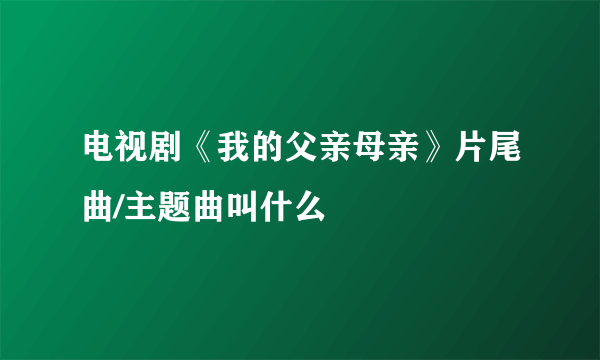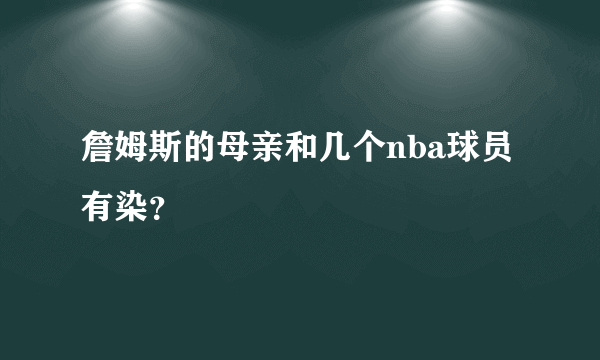我的母亲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小孩子们都讲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妈妈,文学家、科学家、革命家都讲自己的母亲是最伟大的母亲,劳动者都讲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母亲,而且我们每一个人谁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最好的母亲——是母亲将我们带到人世,是母亲的乳汁哺育了我们儿时幼小的生命,是母亲的教诲培养我们健康成长,使我们终于成为今天的我们。
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母亲,既不“美丽”,也不“伟大”,她只不过就是世界上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位母亲,劳动大众、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母亲出生于1916年古历十一月初七,排行老二,上面是一个姐姐,即后来直至我1973年读大学前离村时都一直与我们同住在一个村(生产队)的我的姨妈。
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有几位兄弟,他们都住在一个院子里,相处得十分和睦,是解放初期临利县尺八口地区有名的蔡刘村的大户人家,所以我的母亲姓刘,这儿理所当然地也是我的血脉发源地之一。
母亲是36岁生的我,在我的上面,母亲唯一只生育了我的姐姐,比我大9岁,如今已经是从乡级行政干部位置上退休的老共产党员。我的下面,母亲生育了三个子女,除了一个比我小5岁的妹妹已经是失业多年且退休的工人外,其他还有二位在我出生后的三年内相继出生却在出生时即已经夭折。
为什么是这样?据我老姐讲,我妈妈年轻时算过一命,算命的先生讲,我母亲的命里只能载有润年润月出生的子女。刚好,我们仨都是润年润月出生的。看来算命先生有时也还是讲得比较准的,尽管我并不太相信那些人的话。
从我儿时起,我就知道妈妈是一位小脚女人。我小时问过妈妈,妈妈,为什么您的脚那样小?真的很小,不到5寸长,而我姨妈的脚更小,最多也就三寸长。老妈讲,旧社会,女人都要裹脚,尤其是有钱人家的女孩更要裹脚,以小脚为美。后来长大了我在书中看到有“三寸金莲”之说,就是指此。
老妈讲,当时女孩子裹脚,至少在13岁以前就得裹,用很长的布带,将脚紧紧地缠住。由于裹得紧,疼痛异常,根本就不能下地行走,且必须得忍住疼痛。疼痛时可以哭、可以叫,但就是不能松绑。裹脚开始后,头些日子每次裹脚连续至少一二个时辰,然后松绑一二个时辰,即使松绑了,也疼痛异常而不能行走,接着再裹;经过几天的时间下来,裹脚时疼痛有所减轻,则延长每次的裹脚时间,并相应减少松绑的时间,直至完全不再疼痛,就不再松绑,只有在晚上洗脚前才松解下来。这样到了成年,也就形成了白天自觉裹脚的习惯。
如果不太讲究卫生的人几天裹脚而不洗脚,再一松绑时,那就是中国语言文学作品中曾经写到的一句名言——“王大妈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我妈是13岁时裹的脚,年龄已经偏大,所以脚也就稍微大一点儿,但裹脚时的疼痛折磨就更加厉害;而我的姨妈就更惨了,只有十岁不到就裹脚了,她老人家的脚比我妈的脚更小,是标准的“三寸金莲”,也因此“美丽”的条件,终于也就嫁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公子,那就是我的姨父,姓汪,解放后在我们村划为地主成份,文革时受尽了批斗,也包括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我对他的勇敢的批斗。
不过我姨父的几个儿子都比我大一些,文革结束后,还当上了村小组的干部,孙子也有的成了地方干部,有的成了高级知识分子,子孙幸福,仍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大户人家”。
妈妈是一位勤劳的女性。
从我记事起就没有看到过妈妈坐下来实在地休息过,有时看到她到别人家串门,不知是借东西,还是还东西,但总是不多时就回来做家务。
乃至在妈妈八十岁后,我每次回家仍然看到我的老妈在为儿孙做家务,扫地、做饭、抹桌子椅子,继续不停地干着那些家务小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解放以后新中国最艰苦的年代。
那些岁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妈妈的晚上都是在剁猪菜、煮猪菜,每当半夜叮叮当当的刀剁野菜的响声将我惊醒,我就从睡梦中起床,来到堂屋,只见母亲与父亲还在忙着那些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杂活。
我嘟啷着要他们也去睡,此时母亲就过来牵着我的手,将我再带到房内睡觉,并说,明天还要出工(到生产队做农活),晚上不做完这些事,白天就做不了,你先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我们把事情做完了就会睡的。
但是,待到我再醒来时,已经是天光了,父亲和母亲早已经起床,开始了又一个新的一天的劳作。
妈妈干家务活自然是非常地卖力,因为不卖力,生活就会很困难。
如果能利用每天从生队收工回家后的时间多干点家务,比如多养一只鸡,就能有鸡蛋(有几年时间,上面规定,家中连鸡也是不允许养的,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更不说养猪、养牛了),有鸡蛋就能卖一点钱,再去买一些其他日常用品;努力家务,才有可能将一头猪在喂养8个月至10个月的时间内卖出,就能赚到几十元钱,从而至少半年内的生活稍有宽松。
因此,父亲与母亲总是不辞劳苦地日夜操劳,一般能做到每年喂20几只鸡,出栏一、二头猪,生活也还算过得去,可以供我的姐姐上学的费用。
要知道,我的姐姐是初中毕业生,是我们整个生产大队几百户人家中唯一的女中学生。如果不勤于家务的家庭,生活就显得特别的艰苦。
妈妈从不辞劳苦,在大跃进的年代,谁也不辞劳苦。为生产队出工,夜以继日。大约在我7岁的那年,有一天晚上九时多,母亲与生产队其他人一样仍然在距家约2华里的地方出工,只有我和一岁半的妹妹在家。
当时妹妹正在生病,晚上突然发高烧,我手足无措,也就啼哭不止,隔壁的一位姨娘刚好未出工,她知道后,即赶紧通过一位生产队干部去通知我的母亲。
母亲视力差,因小时生病致右眼有大片状翳障,即角膜瘢痕(所以我讲我的母亲并不“美丽”),晚上在对面火把的照耀下,看路不清,加之心急,从三四米高的陡峭堤坡上重重地跌了下来,当时就人事不醒,还是那位生产队干部将我的母亲背至家中,并为母亲和小妹求医看病。
因为当时父亲为生产队出工在数十里外的地方。
幸亏老天照顾,母亲并没有过于严重的损伤,只休息了几天就继续参加生产队的出工,但从此落下了天气变化就头痛、腰腿痛的毛病。
母亲性格温顺,无论是在我祖父母面前,或者在我父亲面前,或者在五个妯娣之中,还是在生产队其他邻里面前,从来都是语言温和,从来就不高声恶语,母亲活了九十三岁,她从没有与公公婆婆顶过一句嘴,没有与父亲真正红过脸,没有与妯娣发生过一点不愉快,也没有与邻里发生过任何争吵,更没有打过我们几姊妹,有时将她惹急了,也曾经试着要打的样子,但高高扬起的巴掌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落在我们的身上。母亲心地善良,看到他人有难,能够帮助时尽可能地帮助。还是我几岁时,有一位20岁左右的大姑娘手提一个包袱来到我家。
当时我正在家中,母亲在屋后打理菜园子的事情。
我以为是客人,于是将她带到母亲面前。
母亲与姑娘交谈了一会儿,得知姑娘是逃荒至此,离我们家也就是几十里路并不很远,于是欣然同意姑娘留下,答应她住一段时日,想走时再走,这样既能解他人之急,也为自己添了一个照看家里的帮手,因为当时父亲受生产队的派遣长年在外,而我与妹妹也都还小,姐姐读中学寄宿不回家。
可两三天不到,在母亲出工时,姑娘将家中的十多个鸡蛋,以及其他的什么东西——至今我亦未明白还拿了些什么东西,因为母亲并没有细讲,只是说那个姑娘没有打招呼——就自己就走了。
如今想来,这位当年的姑娘已是七十出头的老太。
母亲就是这样的人,从不计较这些小的不愉快,只要对别人能够提供帮助的,她都尽可能地提供。因此,我们家的客人很多,对于那种无关无系的客人,在我小的时候恐怕最多的就是算命先生与讨饭的人。
父亲在家时,经常有男算命先生在家中过夜;无论父亲是否在家,只要是女性的算命先生,都可以在我家留宿。
我的名字,就是一位算命先生给起的。原本我并无名字,小名“丑货”——乡下人认为,名字取得贱好养,不会短命。可能是由于算命先生要在我家过夜吧,过一夜至少还要给他免费供应晚餐与早餐,算命先生硬要给我看相算命不收费,并尽捡好听的讲。
母亲与父亲当然是听得美滋滋的,于是我就有了正儿八经的名字——皇城,文革时期,我将名字改为了更便于书写的同音字。虽然我并未如父母新期望的那样有作为,仍我也仍然是父母的骄傲。
我一九七三年才进入大学校门20天,我的父亲就去世了,因为肺气肿(长期喘息性支气管炎所致)致慢性心衰而殁。这样,家中就只有母亲与妹妹两人生活了,因为姐姐早就出嫁且为人母。还好,在父亲去世的时候,除了我的姐姐妹妹都在他的身边以外,还有一位漂亮的姑娘也在埸,虽然我的父亲当时只知道她是我们大队的领导干部,但她却代表了我,这是天意。因为她就是我妻子,她是在我父亲去世几年后才与我谈婚论嫁的。自从我离家求学并参加工作后,我就很少回到家乡,虽然并不算太远。后来,由于种种情况的变化,我妈妈迁到了岳阳市,与妹妹、妹夫住在一起,与姐姐也就相隔两栋之遥。
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是愉快的。这也是我的心愿。当母亲九十高寿之时,我的同事与同学来到岳阳为母亲祝寿,这是我第一次为母亲祝寿,以后还有二次仅为家人。因为我与我的母亲都不喜欢搞祝寿活动。
母亲走后,我们将她老人家的骨灰安放到了监利县尺八镇上沙村,与父亲相伴而葬。那里是父亲出生的地方,也是父亲长眠的地方。
父亲(五兄弟,排行老三)因为逃避壮丁于1943年与我的母亲和姐姐一起离开此地而迁居湖南(现君山区)。
当年离开老家时,伯父的女儿将要出生,以此为契,两姐妹一名“逃之”(桃芝,桃枝),一名“兵之”(李兵英,1943年农历冬月初六出生),意即逃避当壮丁的年代出生。
母亲去世后次年,在父母亲与已过世的家族其他亲人的万年居址,我请弟侄们重新进行了修茸,并在四周植上了万年松。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位平凡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祝我的母亲、父亲永远安息。
(2011年5月1日,写于长沙)